關于美德的正義:儒家對桑德爾正義觀的修改
作者:黃勇
來源:《南國學術》2017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一月三旬日戊申
耶穌2018月1月16日
《南國學術》編者按:黃勇傳授認為:哈佛年夜學傳授桑德爾反對功利主義和不受拘束主義的正義觀,提出了一種亞里士多德主義的正義觀。這種正義觀,一方面強調正義是一種美德,另一方面又堅持一種以美德為根據并以目標論為導向的分派原則。具體來說,正義就是依照(相關的)美德來分派東西,以認可、尊敬、祝賀和獎賞有德之人,并懲罰那些缺少美德甚至具有惡德之人﹔而要確定哪些美德與所分派的東西相關,則要看所分派的東西所服務的目標。例如,分派年夜學的教職需求追問這些教職的目標。假設這些教職的目標是傳授知識,那么,就應該將教職分派給那些具有有助于實現這個目標的美德之人,即那些擁有相關知識并能將這些知識傳授給學台灣包養生的人。在中國,儒家雖然批準正義是美德,但把作為個人美德的正義與作為社會軌制的美德的正義區分開的同時,又強調這兩者之間的聯系:后者以前者為基礎。相較于桑德爾以美德為根據的正義,儒家更強調關于美德的正義,即關于美德之分派的正義。當發現一個社會中有些人具有美德,而另一些人缺少美德時,儒家并不像桑德爾主張的那樣,通過對有德者與缺德者不服均地分派物品來獎勵前者和懲罰后者。相反,儒家將有德者比作身體安康的人,而將缺德者比作身體出缺陷的人。正如人們不會獎勵身體安康的人而懲罰身體出缺陷的人,而是會盡力幫助身體出缺陷的人打消其缺點從而成為安康的人一樣;人們也不應該獎勵有德者而懲罰缺德者,而是應該幫助缺德者戰勝其缺點從而也成為有德者。由于儒家視有些人有德而另一些人缺德為一種非正義的現象,是以,關于美德的正義也就是盡力使每個人都成為有德者。雖然桑德爾的亞里士多德主義正義觀也認為國家有義務讓其國民成為有德者,但與儒家的一個主要差別是,前者認為這種品德教導的任務重要是通過立法完成的,而后者則強調德教和禮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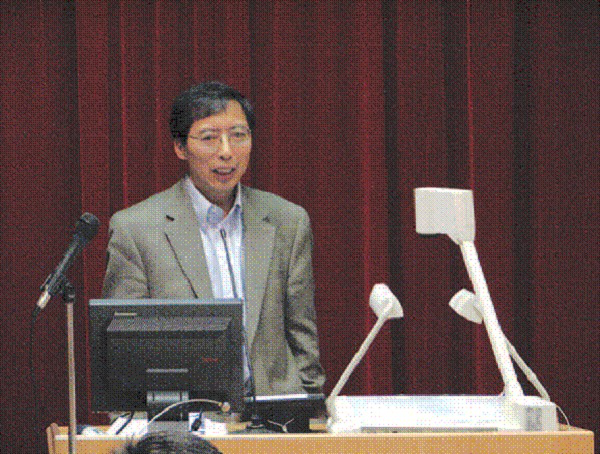
黃勇,1988年在復旦年夜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96年任教于庫茲敦年夜學,1998年在哈佛年夜學獲神學博士學位,1999—2001年任american中國哲學家協會主席,2006年任哥倫比亞年夜學宋明儒學討論班配合主任,2010年任american宗教學會儒家傳統組配合主任,創辦并主編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道:比較哲學雜志》,德國斯普林格出書社出書);現為噴鼻港中文年夜學哲學系傳授,重要從事政治哲學、倫理學、宗教哲學、中國哲學和中西比較哲學研討,代表性英文著作有《宗教之善與政治正義:超出不受拘束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品德的動機》《孔子》,中文著作有《全球化時代的倫理》《全球化時代的宗教》《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等。
導言
在《正義:該若何做是好?》(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一書中,包養app哈佛年夜學傳授桑德爾(Michael J.Sandel)考核了三種正義觀:(1)功利主義認為,正義是福祉或幸福的最年夜化;(2)不受拘束主義認為,正義即尊敬不受拘束與人的尊嚴;(3)亞里士多德主義認為,正義是認可、推重和獎勵美德。對于這三種分歧的觀正義,桑德爾并非一視同仁。他認為,主導當代政治哲學的前兩種正義觀十全十美,他本身努力于提出一種亞里士多德主義理論。【注1】這種理論有兩個重要特征,即“作為美德之正義”(justice as a virtue)和“依據美德之正義”(justice according to virtues)。
根據這樣一種正義觀,一方面,正義的感化不只是協調一個群體的活動并對由此產生的結果加以分派,否則一個黑幫內部奉行的規則也能夠被視作正義。是以,桑德爾在其晚期著作中主張,“假如正義的增長并不用然意味著一種絕對的品德進步,那么,人們就會看到在有些情況下,正義并不是美德而是惡德”【注2】。為了確保正義是美德而非惡德,人們必須采用亞里士多德主義的目標論,把正義作為一種出色品德,使人類發揮其獨特的效能,實現其獨特的完滿。恰是在此意義上,桑德爾認為,“有關正義和權利的爭論,必定要依賴某種關于完滿生涯的特定觀念,而不論我們能否承認它”【注3】;也正因為這般,他不贊成不受拘束主義的見解(以羅爾斯為代表):對于宗教和形而上學的完美概念,人們的正義概念應該堅持中立。
另一方面,桑德爾強調,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的政治哲學中有兩個相關的焦點觀點:“其一,正義是目標論的。對于權利的界定請求我們弄清楚所討論的社會實踐的目標(telos,即意圖、目標或天性)。其二,正義是榮譽性的。為了思慮或討論一種行為的目標,至多有部門任務是思慮或討論它應當尊敬或獎勵何種美德。”【注4】在解釋桑德爾的意思之前,有需要說明,他在這里談論的目標論,分歧于作為美德之正義所觸及的目標論。后一種目標論關注人類生涯自己之目標,依據它可以把一種品德界定為善或惡。但是,前一種目標論關注的是特定社會實踐的目標。例如,分派年夜學教職需求追問年夜學的目標。這就是桑德爾所認為的亞里士多德政治哲學的第一個焦點觀點。第二個觀點與此親密相關,因為恰是社會實踐的目標告訴人們,一個人為了獲得想要的東西應該具有何種美德。【注5】就一所年夜學來說,一個人必須在相關知識和教學技巧方面出類拔萃才幹獲得教職。在這個意義上,正義就是依照(相關的)美德來分派東西,以認可、尊敬、祝賀、獎賞有德之人,并懲罰那些缺少美德甚至具有惡德之人。【注6】桑德爾舉了良多例子來說明本身的觀點,這里可以概述此中的兩個。在正例方面,桑德爾說起“紫心勛章”(the purple heart)的分派:“除了能帶來榮譽之外,這枚獎章還能使獲得者在老兵醫院享有諸多特權……真正的問題在于獎章的意義及其所推重的美德。那么,相關的美德是什么呢?不像其他的軍功章,紫心勛章推重犧牲而非英勇。”【注7】在反例方面,桑德爾提到american當局短期包養對華爾街某些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中經營掉敗的公司實施救助。公眾對救助計劃覺得憤慨,特別是因為一些資金被用于向那些公司的高管發放獎金。誠如桑德爾所言:“公眾認為這在品德上是難以接收的。不僅僅是這些獎金,整個經濟支援計劃似乎都是在有悖常理地獎勵貪婪的行為而不是懲罰它。”【注8】簡言之,正義在此意義上請求獎善懲惡。
但是在我看來,討論作為美德的正義時,厘清作為一種個人美德的正義與作為一種社會軌制之美德的正義的關系,是至關主要的。而中國儒家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有著非常獨特的貢獻。是以,在討論依據美德之正義時,本文將發展出一種“關于美德之正義”(justice of virtues)的儒家觀點,以修改桑德爾的正義概念。
一、作為美德之正義
說正義是一種美德似乎沒什么問題,並且中國儒學總體上認同這一點。不過,有個問題必須講明白。當人們說正義是一種美德而不是惡德時,所謂的美德、包養網單次惡德,最後指的是個人的品德。正義的其他含義,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例如,我們能夠會說某一行為是正義的,這意味著這個行為來自具有正義品德的人;我們也能夠說某一事態是正義的,這意味著它產生于具有正義品德的人(人們)。【注9】這與安康有點類似,安康最後的意思與人的身體有關。在派生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吃的食品很安康,環境無益于安康,或許或人做了一個對安康無益的決定,這意味著它們都與人的身體安康有關。
就此而言,正義是一種個人美德。但是,當代關于正義的討論在很年夜水平上遭到american倫理學家羅爾斯(J.B.Rawls.1921—2002)《正義論》的啟發,所謂正義——假如不是獨一的話——起首與社會正義有關。它所討論的重要問題,不是一個人在與別人互動或處理互動的過程中正義與否,以及在何種意義上、多年夜水平上、若何正義;而是一個社會在管理成員之間的互動方面正義與否,以及在何種意義上、多年夜水平上、若何正義。恰是在此意義上,羅爾斯有一句名言:“正義是社會軌制的重要美德。”【注10】是以,這里的正義不是個人美德,而是社會軌制的美德。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假如正義作為一種美德有兩種含義(作為個人美德的正義,作為社會軌制之美德的正義)的話,那么,它們之間的關系若何呢?
萊巴爾(Mark Lebar)區分了連接二者的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認為個人美德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個體之間的正義關系構成政治軌制的正義。依照這一懂得,我們起首看有德之人試圖維持的與別人的關系是怎樣的……然后追問何種軌制和公共規則可以允許和維持這些關系”;相反,“第二種方法……認為,作為國家構成要素的軌制、實踐等等的結構之正義(國家這一政治實體是社會正義、軌制正義或政治正義等屬性的重要載體)才具有邏輯的優先性。這里,至關主要的是,我們了解正義的社會……應該是什么樣子……根據其作為這個社會的成員所具有的義務和來由,我們可以從這個結構中推表演正義的個體所具有的責任”。【注11】第一種方法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注12】,而第二種則以羅爾斯為代表。不過,在我看來,這兩種方法都是成問題的。
按照亞里士多德模子,社會軌制的正義源自于個體正義。這正確地強調了當局促使人們有德(在現在這一特定的情況下則是正義這種德)的主要感化。但是,這種形式假定,當且僅當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正義地行動,社會正義才幹實現。進一個步驟的假定則是,無論是在分派方面還是在矯正方面,一切正義都由個體而非當局來完成。第一個假定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假如這樣,只需一人不義,社會就不成能正義。至于第二個假定,在一個陳舊的小城邦中或許確實還有一些公道性,但在一個當代的年夜型平易近族國家中顯然是不成能的。例如,american緬因州的一位農夫不成能了解,在舊金山能否有、以及有幾多無家可歸的人值得擁有他所生產的東西。在這般年夜型的社會里,資源的分派必須由國家來完成。僅有個體成員的正義是不夠的;國家所做的分派和矯正也應該是正義的。
這似乎恰是第二種模子的氣力地點。該形式以羅爾斯為代表,強調正義是一種社會軌制的美德。問題在于,它若何與作為一種個體品德的正義相關。羅爾斯的正義原則是人們在原初狀態之下選擇的,是以,人們或許可以說,這些正義原則反應或表達了這些在原初狀態中的人的美德或正義品性。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羅爾斯的社會軌制正義同樣源自個體正義。但是,這一解釋顯然不成立。因為,如羅爾斯所述,原初狀態的人起首都只關心本身的好處,而漠視別人的好處,是以不成能認為他們是有德的(在普通意義上)或正義的(在特定意義上)。【注13】正確的懂得是,羅爾斯把原初狀態作為一種決定社會軌制正義原則的獨立法式。在他看來,雖然我們了解以這種方法獨立決定的規定社會軌制的正義原則必須是正義原則,可是,假如社會中的個體不接收這樣的原則,社會就會不穩定;是以,從童年開始培養個體的正義感就很主要。例如,羅爾斯認為,“當軌制正義時……那些參與這些社會設定的人們就會獲得相應的正義感和盡力維護這些軌制的欲看”【注14】。但是,即便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對社會軌制而言確實是正義原則,由于推衍這些正義原則的過程絲毫沒有考慮(使人成為人的)人類天性,運用它們來決定作為一種個人品德的正義這種美德本質上是成問題的。每一個體應該具有的美德乃是讓他們成為完滿之人的品德;假如不了解什么是人道,就不成能懂得什么能使人成為完滿之人;可是,在原初狀態中選擇正義原則的人那里,任何人道概念都被明確消除在外了。也許,恰是在這個意義上,萊巴爾對這樣的政治正義概念有所不滿,因為羅爾斯“能夠會以始料未及的方法限制個體正義的能夠性”【注15】。
鑒于連接兩種正義的這兩種方法都沒有盼望,萊巴爾哀嘆:“我們能夠無法看到,作為個體美德的正義概念可以和軌制正義相分歧。”【注16】但是,我認為有來由加倍樂觀地對待這一問題。這里,我想到的是美德倫理學家斯洛特(Michael Slote)的進路。按照他最新的美德倫理學,有德之人具有“同感”(empathy)才能,而“同感”被視作一種美德。為清楚釋那種關聯,斯洛特認為,“一個既定社會的法令、軌制和習俗就像該社會的行為”;正如個人行為反應或表達主體的品性,一個社會的法令、軌制和習俗反應或表達創造它們的社會群體的品性:“是以,一種以同感關懷為基礎的感情主義倫理學能夠說,假如軌制和法令、以及社會習俗和慣例可以反應出那些負責制訂和維持它們的人所具有的同感的關懷動機,那么它們就是正義的。”【注17】斯洛特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作為社會軌制之美德的正義由作為個人美德的正義派生而來。就此而言,他們的進路是附近的。其區別在于,在亞里士多德的模子中,作為社會軌制之美德的正義旨在培養正義的人;而在斯洛特的模子中,作為社會軌制之美德的正義確保個體之間的互動或來往是正義的。
中國儒家年夜體上會接收斯洛特的觀點,認為社會軌制的正義反應了領導人的品德品性。他們的“內圣外王”觀念就表達了這個思惟。外王,即政治軌制,僅僅是內圣即品德美德的表現。例如,孟子(約前372—前289)說:“全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18】“四書”之一的《年夜學》作了進一個步驟的發揮:“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是說,當局是善的(普通意義上)或正義的(特定意義上),只是因為管理它的人是善的。孟子還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全國可運之掌上。”【注19】這里他強調,因為領導人有德,當局也就有德。
不過,中國儒家也不完整批準斯洛特的觀點,因為他們的請求要高得多。斯洛特認為,一項法令假如體現或表達了立法者的同感動機就是正義的;但同時他也承認,“一項法令只需沒有反應或表現出它的制訂者之適當的同感關切之缺掉,它也能夠是正義的”。【注20】他解釋道:“品德敗壞的國家立法者,對同胞福祉和國家好處漠不關心,但能夠通過一項不會體現或反應其貪婪和無私的法令。例如,假如他們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允許車輛在亮紅燈的路口右轉的法令,那么這項法令還是正義的,或許至多不是不正義的。”【注21】斯洛特在社會的正義法令和個人的正義行為之間進行過模擬。假如回到這個模擬,我們便可以看到斯洛特作出以上讓步的問題。斯洛特所想的是,不具備美德或許甚至具有惡德的立法者所制訂的法令,假如沒有反應其惡德,能夠與那些體現并表達有德的立法者之美德的法令無異。這就似乎一個具有惡德之人所做的工作,假如沒有反應其惡德,也能夠與一個具有美德之人的行為沒有分歧。我們了解,這種具有惡德的人的行為不克不及被視作有德的行為,而只能視為符合美德的行為。但是,亞里士多德指出:“符合美德的行為并不因它們具有某種性質就是(譬如說)正義的或節制的。除了具有某種性質,這個行為者還必須處于某種特定的狀態。起首,他必須了解那種行為。其次,他必須經過選擇而那樣做,并且因那行為本身之故而選擇它。再次,他必須出于一種確定了的、穩定的質量而那樣選擇。”【注22】他進一個步驟指出:“有些行為之所所以正義的或節制的行為,是因為它們是以正義的和有節制的人所具有的方法做出的行為。一個人被稱為正義的人或節制的人,并不僅僅是他做了這樣的行為,而是因為他像正義的或節制的人那樣地做了這樣的行為。”【注23】恰是出于這個緣由,儒家總是強調一個人不僅應該做正派之事,並且應該由正派之心往做。是以,孟子贊揚圣人舜,說他“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注24】。
人們能夠會問,一項內容雷同的法令出自正義的人或不正義的人,二者之間畢竟存在何種實際的差別。一個能夠的答覆,尤其是從儒家角度來看,是法令永遠不成能完善,總是有破綻。若把一項法令僅僅視作一項法令,我們傾向于從字面上對待它,是以能夠會被引導往做一些明顯不正義但并不違法的工作。相反,若把法令看作是立法者美德的表達和反應,我們傾向于強調它的精力,是以即便法令允許甚至請求我們往做,我們也不會被引導往做一些明顯不正義的工作。這里就用斯洛特舉過的例子:法令允許司機紅燈時右轉。假如只把它當作一項法令,那么,哪怕在路況擁堵紅燈右轉會梗塞路口時,或許在看到一輛車從相反的標的目的(不符合法令)左轉時,我們能夠還是會試圖在紅燈時右轉,因為這是符合法規的。但是,假如我們認為法令反應了立法者的美德,我們就不會這樣做,因為我們可以懂得,這樣的行為不成能是有德之人愿意我們往做的。這里也可以用羅爾斯的差別原則作為另一個例子。假設這個原則是正義的,也就是說,它符合立法者(或政治哲學家)的美德,但它并不是由一位有包養留言板德的立法者(或政治哲學家)制訂的。假如我是才華出眾的人,該原則對我來說意味著,除非我的薪水比別人高,否則我就不充足發揮我的才幹讓平淡者獲得最年夜的益處;假如我屬于平淡之輩,該原則意味著,我不會允許一個有才華的人賺得更多,除非他充足發揮其才幹讓我受害。【注25】可是,假如我們認為該原則不止是符合立法者的正義品性,而是實際上就是正義的;也就是說,它反應和表達了立法者的正義這種美德,那么,假如我才華出眾,就會把該原則的意圖懂得為,我應充足發揮才幹以最有用的方法讓平淡者受害。是以,即便我的薪水不比別人高,我依然會充足發揮我的才幹(盡管不太不難說,平淡者該若何若何)。【注26】
二、依據美德之正義,抑或關于美德之正義?
接下來轉向桑德爾的新亞里士多德主義正義觀的第二個特征,我將其描寫為“依據美德之正義”:分派某物,要根據其所認可、推重和獎賞的相關功績、出色或美德。這一正義概念最適用的領域似乎是分派職位、尤其是政治職位和榮譽,但在分派經濟好處方面卻不盡然。例如,現在重要是以貨幣的情勢分派經濟好處。假如是長笛或其他特定的實體,它們還能夠有一個目標,后者可以說明我們確定,在分派它們的時候何種相關的美德需求考慮。可是,假如追問貨幣的目標(用來買什么東西)和它所認可、推重、獎賞的美德(擅長投資或討價還價),便幾多有點希奇。社會機構供給的多種服務亦是這般。例如,醫院的目標是供給醫療衛生服務,是以,應該向那些能夠比別人更好地服務于這個目標人供給醫生職位。但是,若問應該若何分派醫院供給的醫療服務,以及病人應該具備哪些美德來獲得這些服務,則顯得有些希奇。或許可以說,應該根據人們對社會的貢獻水平分派財富和醫療(服務)。這種觀點似乎符合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但是,羅爾斯會覺得這很是令人難以相信,因為偶爾的天然和社會原因會影響人們對社會所做的貢獻鉅細,不應該由此決定他們應該分派到幾多。
桑德爾的一些主張讓人覺得,他的“依據美德之正義”似乎是一種廣泛的分派原則,適用于任何被分派的事物。【注27】不過,有時他似乎把它限制于榮譽和政治職位的分派。如上文所言,他的依據美德之正義在這些領域的應用最為公道。至多有兩種跡象表白,桑德爾堅持這種受限較多因此也較為公道的觀點。第一個跡象,他在比較亞里士多德和當代政治哲學家時認為:“明天我們討論分派正義的時候,重要關心的是支出、財富和機會的分派。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分派正義重要不是關于金錢,而是關于職位和榮譽。”【注28】人們有來由認為,桑德爾講依據美德之正義,心里想的重要是職位和榮譽。第二個跡象在于,桑德爾確定“應得”(desert)概念至多是公正分派的部門基礎。眾所周知,羅爾斯對基于應得的分派正義提出了強無力的反駁,因為他主張,由于偶爾的天然和社會事務的影響,無人應得任何東西。桑德爾討論羅爾斯正義理論的這部門內容時持很是贊許的態度。【注29】即便他(至多在必定水平上)試圖捍衛“應得”概念,他依然聲稱羅爾斯的觀點在品德上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它消除了精英社會中人們所熟習的那種自以為是的空想:勝利乃美德之冠,窮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們比窮人應得的更多”。【注30】當然他也主張,羅爾斯的觀點“令人不安”,因為“從政治上或哲學上來說,我們不成能使關于正義的論證脫離關于應得的爭論”。【注31】不過,當他提出這樣的主張時,他所舉的例子包含“就業和機會”【注32】,以及諸如“學校、年夜學、職位、職業、公共職位”等問題。事實上,整個討論以年夜學進學政策結束【注33】。
不論怎樣,即使是桑德爾正義觀最言之成理的部門:根據職位(特別是政治職位)——依其目標——所認可、獎勵、推重的美德對職位進行分派,中國儒家也會深表迷惑。解釋儒家這一迷惑的最好方式,就是強調儒家正義觀的一個面向。它不僅與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包含桑德爾所發展的版本)相分歧,並且實際上也可以成為其組成部門。我稱之為“關于美德之正義”【注34】。簡言之,假如桑德爾的“依據美德之正義”是關于依據美德來分派某些事物的正義,那么儒家的“關于美德之正義”即是關于美德本身的分派正義。換句話說,假如桑德爾的“依據美德之正義”認為政治職位是被分派的東西,那么,儒家的“關于美德之正義”把政治職位視為可以用來分派美德的東西之一。
在任何一個社會里,最能夠的是,有些人具有美德,有些人缺少美德或許具有惡德。換言之,人們并分歧樣地擁有美德。在討論正義請求人們若何處理這樣一種狀態之前,起首需求清楚美德以及惡德的本質。儒家的美德觀采用了一種安康模子。根據這個模子,有德之人猶如安康的人,而惡人猶如身體忍耐疾病熬煎的人。例如,孟子把人皆有“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長短之心)比作有“四體”【注35】,把品德與身體聯系了起來。王陽明(1472—1529)是明代最具影響力的理學家之一,他把一個缺少美德的人或邪惡之人比作身處懸崖邊的人。就像后者即使免于一逝世也將遭遇宏大的身體傷害,前者將遭遇內在的傷害。【注36】假如有什么分歧的話,人的內在安康即美德比內在安康即身體安康加倍主要。是以,當二者發生沖突時,應當照顧前者而非后者。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子做了有名的“小體”(肉身)“年夜體”(品德心)之區分,譏笑人們關心處理大事的小體而忽視處理年夜事的年夜體:“體有貴賤,有小年夜。無以小害年夜,無以賤害貴。……養其一指而掉其肩背,而不知也。”【注37】
這樣的觀點,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并不生疏。他也經常比較身體的安康和靈魂的安康。譬如,他認為,只聽醫生的話不會使病人身體安康;同樣,只聽哲學家的話不會使人們靈魂安康。【注38】《尼各馬可倫理學》中關于正義的討論甫一開始,亞里士多德便對一個幹事正義的正義之人和一個安康步行的安康之人進行了模擬。【注39】事實上,當他對愛本身內在幸福的粗鄙的自愛者與愛本身美德的真正的自愛者進行對比時【注40】,他的觀點與儒家的觀點相分歧:人的內在安康比人的內在安康加倍主要。
這樣一來,就很明顯,假如有人有美德而又有人有惡德,正義請求我們做的,不是獎賞有美德的人、懲罰有惡德的人,而是幫助后者擺脫惡德成為有德之人,正如當我們發現安康的人和病人時,正義請求我們所做的不是獎賞前者懲罰后者,而是設法治愈或減輕后者的疾病。也許有人會說,把身體上的安康與品性上的美德相模擬是不恰當的,因為人的安康超越人的把持范圍,而人的品性則在把持范圍之內。但是,這種說法并不完整正確。一方面,好比通過堅持運動、遠離煙草、攝進安康的食品以及堅持充分睡眠,人的安康很年夜水平上在可控范圍內;另一方面,人的品性并不完整在一個人的掌控之中。
關于第二點,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家有過一個很好的解釋。再以王陽明為例。在王陽明看來,一個人之所以缺少美德或具有惡德至多觸及兩個其無法把持的原因。起首,王陽明提到了與生俱來的“氣”或“氣質”。王陽明認為:“知己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殘餘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殘餘原少,無多障蔽,略加努力之功,此知己便自瑩徹,些少殘餘如湯中浮雪,若何能作障蔽?”【注41】當代哲學家特別是受過東方哲學傳統訓練者,能夠會發現王氏對“氣”的形上學討論很繁瑣且難以懂得,但良多人生怕也批準他試圖闡發的要點:正如人生成的天然稟賦存在著天然的不服等,人的後天品德質量也能夠存在著天然的不服等。至多亞里士多德也持類似觀點。例如,他區分了素性有品德感的人和生成不遵從羞恥感的人【注42】;當有人認為一個人好是生成的時,他回應說:“天性使然的東西顯然非人力所及,而是由一些神圣的緣由賦予那些真正幸運的人的。”【注43】他還說,應該對“本性拙劣的人”實施懲罰和管制【注44】。
其次,王陽明強調環境影響對一個人性德品性的主要性。在援用“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這兩句古話之后,他接著說,風俗之善惡,是習性長期積累形成的結果,從而影響生涯于此中的人的品德質量:“往者新平易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異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注45】這包含缺少晚期的家庭品德教導,缺掉傑出行為的安慰,以及他們被別人的憤怒咒罵進一個步驟推向邪惡。是以,王陽明斷言,假如有人逐漸墮進罪惡,無論是有司(當局)還是怙恃和鄰居都難逃其咎。假如王陽明認為人們生成的品德素質不服等的觀點在某些人看來依然頗具爭議,那么,他關于環境影響人們品德教養的觀點顯然不存在爭議。例如,羅爾斯認為,不僅人們生成的才能和稟賦不難遭到天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限制,並且他們的美德也不完整是他們本身的:“有人認為,獲得使我們能夠往盡力培養我們的才能的優越品性乃是我們本身的功勞,這樣的論斷同樣是成問題的,因為這樣的品性在很年夜水平上依賴于我們晚期生涯所處的幸運的家庭和社會環境,而對這些條件我們是沒有任何權利往邀功的。”【注46】
但是,身體安康和品性美德之間的模擬在某些方面的確不克不及成立。一方面,假如一個人的身體存在嚴重的問題,例如身患絕癥,那么在人類文明的現階段、現有醫療技術程度之下,確實無計可施。即便正義請求人們同等地分派身體安康,也能夠無法實現。相反,儒家信任,無論一個人由于何種緣由而變得多麼邪惡,這個人依然可以變成有德之人。換言之,美德的同等分派總是能夠的,這就是為何儒家認為人人可以成圣。另一方面,身體安康與美德相類似,而與長笛和金錢等物質的東西則不類似。在后一種情況之下,或人的長笛好則另一人的長笛就差些,或人金錢多些則另一人就金錢少些,因為這樣的東西無論若何豐富總是無限的。相反,一個人越安康、越有美德,并不料味著另一個人的安康和美德就必定變得越差,因為它們的供給近乎無限。或許我還可以進一個步驟爭辯說,更能夠的是,一個人變得越安康、越有美德,實際上越無益于另一個人變得加倍安康和更有美德。不過,安康與美德之間仍能夠有不類似之處。就身體安康而言,很不難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便一切疾病都是可以治愈的,也會因一部門病人所需求的藥品出現供應缺乏而延誤。這樣就會出現這些藥物若何分派的問題,一個人獲得(更多)藥物而變得安康,當然就意味著另一個人得不到(足夠的)藥物而無法康復。但是,假如是讓沒有美德或有惡德的人變得有德,就很難找到與藥物缺乏類似的情況。
三、“美德”可以分派嗎?
在說明了人們之間正義或同等地分派美德的觀點并不像它乍看起來那樣荒謬之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若何做到這一點?儒家思惟供給了兩種渠道。一方面,需求自我修養。儒家認為,盡管成為惡人并不完整是某個人本身的錯,但這個人至多要部門地對本身成為惡人負責;此外,只需愿意盡力,他也可以成為惡人(誠然,一個人身處的天然與社會條件越是不良或晦氣,他就越是要做出更年夜的盡力)。另一方面,正義請求人們做的——不論作為個體還是政治領袖——不是獎勵惡人懲罰惡人,而是幫助惡人戰勝他們的惡,從而使他們止惡成德。這般一來,美德就可以在一切人中間同等或正義地分派。這里一是修己(自我品德修養),二是立人(品德教導)。【注47】本文重點討論第二個方面。因為,人們現在關心的是,當美德分派發生不正義即不服等時,正義請求人們怎么做?
儒家思惟的一個獨特之處在于,一個人之所以有德,不僅僅是因為這個人幫助那些遭遇饑餓、嚴寒、疾病或其他心理苦楚的人;而是因為這個人想讓別人成為有德之人。【注48】闡明這一儒家思惟的辦法是,弄清儒家黃金律的獨特之處,尤其是通過與其他傳統中類似的品德律作比較。依照東方傳統對于“黃金律”的懂得,一個人應該像他愿意(或不愿意)別人對他做某件事那樣對別人做(或不做)某件事。但是,品德黃金律并不請求一個想要遵守黃金律的人使別人也遵守黃金律。例如,一個人盼望本身身處窘境時有人幫助他,那么依照黃金律,他要幫助身處窘境的人;不過,黃金律并不請求他促使別人也幫助身處窘境的人。一個人不盼望本身遭到不公正待遇,那么依照黃金律,他不克不及待人不公;不過,黃金律并不請求他促使別人也不待人不公。但是,儒家的品德黃金律不止于此。一個人除了應該像他愿意(或不愿意)別人對他做某件事那樣對別人做(或不做)某件事,孔子(前551—前479)還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注49】。“立”的含義很是清楚,就是要培養或實現自我。在孔子那里,這意味著更多關注一個人的內在品性而非一個人的內在幸福。孔子列舉本身主要的性命節點,說到“三十而立”【注50】。毫無疑問,他談論的是本身品性的構成。關于“達”,孔子本身供給了一個定義:“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51】一切這些都明白地表白,“達”重要與一個人的內在幸福、品德質量有關。是以,一言以蔽之,儒家的黃金律從本質來講就是,假如我想成為有德之人,我應該幫助別人成為有德之人;進而,假如我不想成為一個惡人,我應該幫助別人不成為惡人。
最有興趣義的是,孔子在這里用“直”解釋“達”的含義。“達”之人也會幫助別人“達”,而“達”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直”。這種對“直”的懂得可以幫助我們清楚《論語》中兩個包括“直”的困難段落,而假如能夠正確懂得它們,將有助于推進此處討論的問題。在《論語·憲問》中,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以德報怨”是道家老子(前571—前471)所倡導的觀點。【注52】孔子答曰:“何故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畢竟若何懂得?學術界存在爭議,盡管孔子顯然不認同老子或耶穌建議人們對待作惡者的態度,即以德報怨。有人把“直”解讀為“值”,意思是“價值”,認為孔子所說的是,你應該以一種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與怨對等的、年夜致與你遭到的傷害差未幾的價值來報答作惡者。【注53】不過,依照年夜多數學者的見解,孔子教導人們在品德上持中間態度。以怨報怨過于寬容,而以德報怨則過于嚴苛,中間態度就是以一個人當時真正的感觸感染即直來回報惡行。【注54】
我對這兩種解釋都持反對態度。【注55】在我看來,孔子所謂“以直報怨”,就是做一些工作以幫助那個給我形成不當傷害的人即不正派的人,使之成為一個正派的人。無妨看一看孔子若何對比“直”和“枉”。他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56】在統一章中,門生子夏闡明師意:“舜有全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全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同樣,孔子贊揚衛國一位正派的年夜臣史魚。史魚病重,臨逝世前告訴兒子,本身執政未能說服衛靈公選拔賢臣遽伯玉而斥退佞臣彌子瑕。是以之故,他的葬禮不應該在正堂舉行。不久他逝世了,兒子遵囑治喪。衛靈公前來吊唁,問為何這般這般,兒子把父親的遺命告訴了他。衛靈公聞之動容,接收規勸選拔了遽伯玉,罷黜了彌子瑕。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尸諫”故事,而史魚不僅僅被視作“直己”,並且還“直人”(例子中的衛靈公)。孔子感嘆:“直哉史魚!”【注57】他顯然在雙重意義上懂得“直”【注58】。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直”的獨特徵:一個正派的人不僅本身正派,並且還使別人正派。孔子說“好直欠好學,其蔽也絞”【注59】,宋人邢昺疏曰:“君子之曲曰直。”孔子的追隨者孟子也強調了直的這一特點:“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并認為,一個正派的人會使台灣包養網不正派的人變得正派。【注60】《年齡左氏傳》也有正、直連用的表述:“正曲為直。”【注61】
“直”的這一含義,也有助于人們更好地輿解《論語》中出現“直”的另一章有爭議的文字。這章記錄了葉公和孔子之間的對話。葉公對孔子說:“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沒有表揚那個人,而是回應道:“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此中矣。”【注62】這一章是《論語》解經史上的一年夜疑案,在過往十幾年里還成為中國學者爭論的一年夜焦點。爭論雙方都認為,這段文字把人們帶進“孝道”和“社會正義”的兩難窘境。此中一方為孔子將孝道放在社會正義後面辯護,另一方則批評孔子沒有把社會正義放在孝道後面。我曾經主張,爭論雙方都不對。【注63】懂得這一章的關鍵也是“直”。人們已經看到,“直”意味著正枉、正曲。在該章中,父親偷了鄰居的羊,這一事實表白他是不正派的。一個正派的兒子應當使他不正派的父親為人正派。問題在于,兒子不流露他父親的偷竊行為,在何種意義上有利于父親變正派。孔子只是說,正派在于兒子的隱,而不是他的隱自己是正派的。
孔子為人們供給了一條線索。他說:“事怙恃,幾諫。”【注64】當怙恃做了不品德的事,一個人應該和顏悅色、輕聲細語地規勸。這句話意味深長。起首,假如怙恃做了不品德的工作,兒女們不應該只是袖手旁觀,當然更不應該跟著行不善。相反,他們應該規勸怙恃不可不善;假如為時已晚,就要催促怙恃糾正這種情況。是以,假如父親偷了一只羊,一個正派的兒子就應該勸說他加以糾正。這表白,孔子在該章中并沒有倡導以社會正義為代價行孝道。其次,勸說怙恃不做壞事,在這里被視為一種“侍奉”怙恃的方法。換句話說,規勸是行孝的後代應該做的一件主要的工作。遵行孝道并非一味服從怙恃。例如,孔子的門生子貢問孔子,能否服從怙恃便是孝,正如臣下服從君王便是忠。孔子答覆道:“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可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注65】類似的文字也見于《荀子·子道》。這表白,孔子并不以孝道為代價促進社會正義。以上兩點合而表白,對孔子來說,孝與社會正義之間并不存在兩難窘境。再次,要想規勸勝利,就必須溫和地進行。其緣由在于,假如怙恃將要做或已經做了某些不品德的工作,這說明怙恃不是有德之人,所以責罵他們當然不會讓他們意識到錯誤,從而戰勝本身的惡習。假如父親偷了一只羊,兒子向公共機關報告,父親確定會生兒子的氣,他也不成能聽從兒子的規勸。是以,在我們一向在討論的這段文字中,孔子說一個行孝的兒子不應該流露父親偷了羊(這并不料味著掩蓋事實或妨礙公共機關調查它),這是為了創建一個可以更有用地糾正他父親惡德的傑出環境,而這恰好是“直”的含義:使不正派的人變得正派。【注66】
依照包養網評價儒家的“關于美德之正義”(即同等分派美德的正義)的請求,人們不是要獎善懲惡,而是應該幫助惡人戰勝他們的惡習從而使他們變成有德之人,正如依照正義的請求,人們不是要獎勵安康的人而懲罰病人,而是應該幫助病人戰勝疾病變得安康。但這并不料味著人們應該對違法者作寬年夜處理或原諒他們的錯誤行為。【注67】儒家認為,假如有惡人,人們不應該指責他們未能成為有德之人,而是盡力幫助他們祛惡。假如他們仍然行惡,那么,人們應該檢查本身,了解一下狀況在盡力幫助他們時能否有做得不當的處所,了解一下狀況若何進步本身以幫助他們。【注68】但是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儒家堅持認為,不克不及讓惡人繼續行惡,因為他們缺少美德而別人卻擁有美德就是不公正或不正義,就像有人安康而有人生病乏人照顧就是不公正或不正義。
四、儒家若何分歧于亞里士多德主義者
儒家“關于美德之正義”的焦點在于,具有正義這種美德的品德主體——無論是個人還是當局,都應該把培養人們的美德作為本身的目標。但是,這包養網單次聽起來與桑德爾的亞里士多德式的正義并無多年夜差異。桑德爾指出:“對于亞里士多德而言,政治的目標并不在于樹立一套中立于各種目標的權利框架,而是要塑造好國民,培養好質量。”他還援用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來支撐本身的觀點:“任何一個真正的城邦,而不僅僅是名義上的城邦,必須努力于促進善這一目標。否則,一個政治機構就淪為一個單純的聯盟……而不是它應當成為的那種能使城邦的成員變得良善和正義的生涯規則。”【注69】是以,我信任桑甜心寶貝包養網德爾也會接收儒家的“關于美德之正義”。不過,儒家的關于美德之正義觀與桑德爾的亞里士多德主義的依據美德之正義觀還是有一些細微但又很主要的差別;事實上,正因為感觸感染到這些差別,我才認為儒家對后者會有一些保存意見。
起首,盡管儒家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應該讓有德之人擔任政治職務,但他們這樣做的來由至多不盡雷同。桑德爾強調,這些職位的存在是為了認可、獎勵和尊重有品德的人。這一點在他運用亞里士多德關于若何分派最好的長笛的例子中可以看得最為明白。人們能夠會批準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應當把最好的長笛分派給最好的長笛吹奏者。但“緣由安在?”桑德爾自問自答:“嗯,你能夠會說,因為最好的音樂家能吹奏好長笛,創造人人都喜歡的音樂。這是一個功利主義的來由。但并不是亞里士多德的來由。他認為,最好的長笛應當給予最優秀的長笛吹奏者,因為這是長笛的目標——被很好地吹奏。長笛的目標在于產生動聽的音樂,那些能夠最佳地實現這一目標的人應當擁有最好的長笛。”【注70】把最好的長笛給最佳吹奏者,同樣,把最有影響力的職位給最有德的人,桑德爾區分了功利主義的來由和亞里士多德的來由。就此而言,我認為儒家會采取功利主義的來由:【注71】讓有德之人擔任政治職務的來由不是獎勵、尊敬或認可他們,而僅僅因為擔任這些職位能夠使他們更好地發揮其使別人有德的感化。無論若何,有德之人之所以有德,不是因為他們要尋求認可、獎勵或尊敬。這些東西即使對于亞里士多德來說也是內在的東西,是俗氣的自愛者尋求的東西,而真正的自愛者愿意在需要時犧牲這些內在的東西,因為他們所關心的是屬于他們內在幸福的本身的美德。
其次,關于身居政治職位者使人有德的方法,儒家能夠也分歧意包含桑德爾在內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者的觀點。亞里士多德認為,論辯不會起感化,多數人“按其天性所聽從的都不是羞恥感而是恐懼。他們不往做壞事不是由于這些壞事卑劣,而是因為他們懼怕懲罰”。【注72】是以,政治領袖通過制訂法令來完成他們使人有德的任務。他指出:“假如不讓包養行情其在健全的法令下成長,就很難有正確的方法讓一個年輕人變得有美德。因為過節制的、忍受的生涯并不快樂。所以,他們的教養和職業要在法令指導下進行。……因為多數人服從的是法令而不是論證,是懲罰而不是高貴感。”【注73】桑德爾似乎批準亞里士多德的見解,他埋怨說:“對于不受拘束社會中的許多國民來說,品德法令化這一觀念是令人厭惡的,因為它墮入缺少容忍和強迫的危險。”他緊接著說:“但是,正義社會認可某些美德以及完滿生涯的觀念……在意識形態領域中激發了許多政治運動和爭論。”【注74】在另一個處所,桑德爾問道:“一個正義的社會謀求推進其國民的美德嗎?或許,法令能否應該中立于各種分歧的美德觀念?”【注75】其弦外之音,國民的美德可以(假如不是僅僅)通過法令獲得晉陞。
我們已經看到,儒家批準亞里士多德主義的觀點,認為使國民有德是當局的主要職能;他們也批準,這種任務不克不及純粹由論辯來完成。但是,通過立法和實施懲罰性法令使國民有德,這樣的觀點與儒家水乳交融。孔子在《論語·為政》中有句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平易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一段落的前半部門與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截然相反,而我認為孔子顯然是對的。懲罰性的法令不論多么嚴厲,或許能夠禁止人們往做不品德的工作,但卻不克不及使惡人成為有德之人,因為,亞里士多德本身也講,他們“不往做壞事不是出于羞恥,而是因為懼怕懲罰”【注76】。所以,當確信他們的行為不會被發覺并由此不會被懲罰,他們就不會不往做壞事;並且,當他們把持本身不往做很是愿意做的事(壞事),或許嘗試往做他們不樂意做的包養金額工作(功德),他們還將不得不經歷內心的掙扎。這當然晦氣于他們成為有德之人。在該段落的后半部門,孔子建議改用禮儀規范和美德使人有德。禮儀規范分歧于懲罰性的法令。假如人們違反這些規則,不會遭到懲罰,但會被人看不起,因此覺得慚愧。而所謂德治,孔子指的是政治領袖的典范德性。【注77】
由此引出儒家和亞里士多德主義之間的第三點差異。二者都認為當局具有使人有德的效能,並且那些擔任政治職務的人應該擁有美德。不過,這些政治官員畢竟應該擁有哪些相關美德,二者的見解并紛歧樣。亞里士多德強調立法者對于制訂能禁止人們做壞事的懲罰性法令的主要性。這樣的法令,或許不僅能禁止人們做壞事,還能使人變得有德。但問題在于,哪種人有資格成為立法者。換言之,人們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美德才幹被這樣的政治職位所認可、獎賞和尊敬呢?有興趣思的是,亞里士多德拿醫生作模擬。假設你的孩子生病了。一方面,作為怙恃,你了解良多關于孩子的細節。另一方面,有一位醫生,他從沒見過你的孩子。你會本身設法治好你的孩子,還是往看醫生?當然是后者。為什么?因為醫生“具有普通性的知識,理解對于每個人或某類人什么是好的”。【注78】一個人成為一名能夠治病的醫生,不是因為醫生自己是安康的或許至多沒有病人所患的疾病,而是因為醫生擁有治療疾病的相關知識和技巧。同樣,亞里士多德認為,要使一個孩子有德,是立法者而非怙恃的任務。立法者可以發揮這樣的感化,除了他們是立法者這樣簡單的事實而具有的權威之外,還因為他們擁有立法的知識和專業技巧,能夠讓所立之法有用地達到預期的目標,而不僅僅因為他們擁有他們想使人們擁有的美德——因為其他良多人也擁有這樣的包養妹美德。事實上,我們可以把亞里士多德的模擬往前推進一個步驟(這樣做,應該是公道的):立法者通過制訂法令來訓練人們具有美德,而他們能否具有這樣的美德并不主要。醫生可以治病人的病,不是因為他本身沒有病,而是因為他有相應的知識和技巧。假如沒有這樣的知識和技巧,無論醫生多么安康,他都無法治療病人的病;有了這樣的知識和技巧,即便他本身有同樣的病,依然可以治愈病人。同樣,即便一個人沒有當局盼望其國民擁有的美德,只需這個人有足夠的知識和技巧,清楚什么法令可以使人有德,這個人依然有資格成為一名立法者。
對孔子來說,使人們變成有德之士的,并非當局所制訂的法令,而是那些擁有政治職位的人透過其行為所表現出來的典范性美德;政治領袖必須具有他們盡力使國民具有的美德。這可以在《論語》中找到許多根據。孔子對政治統治者的建議幾回再三強調有德的主要性。例如,他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克不及正其身,如君子何?”【注79】此中,“政”是“正”的同源詞。又如,季康子問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進一個步驟問,能否要殺不循道的人,孔子答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平易近善矣。正人之德風,君子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80】在孔子看來,統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81】;“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注82】。《孔子家語·王言解》中有一年夜段文字把這一點說得很明白:“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平易近之本也。……凡上者,平易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
總之,孔子認為政治領袖應該具備的美包養管道德恰好是他們盼望國民擁有的美德。例如,假如想讓國民“誠”,他們必須起首有誠的美德;假如盼望國民“仁”,他們必須起首有仁的美德;假如想讓國民“義”,他們必須起首有義的美德。【注83】比擬之下,依照桑德爾的亞里士多德主義,政治職位的目標是尊敬、認可和獎賞人們,因為他們擁有制訂、執行和宣布可以使國民有德(例如,誠實、善良、正義)的法令的美德或技巧和才能。有時候桑德爾稱這種美德為國民美德【注84】。不過,我認為他將管理國家稱為“靈魂塑造”時描寫得更為準確【注85】。有人也許會為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辯護說,既然政治領袖的任務是使人有德,那么在幻想狀態下,只需他們能對靈魂進行有用的塑培養夠了,但他們本身紛歧定要有德。就像一家汽車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不需求任何制造汽車零部件或把分歧部件組裝成整車的知包養情婦識或才能。他只需具備治理分歧的人以最有用的方法往做分歧的工作的知識、技巧和才能就夠了。【注86】這種對亞里士多德的辯護,沒有留意到品德教導和治理與非品德工作的訓練之間存在主要區別。假如有人教我打籃球,我獨一關心的是他可否教我把籃球打得更好;至于他本身籃球打得好欠好,我并不關心。但是,假如有人教我誠、仁、義,而他本身卻不誠、不仁、不義,那么,假如我還沒做到誠、仁、義,那我就不太能夠認為它們是我應該擁有的美德。
對比儒家“關于美德之正義”與桑德爾亞里士多德式的“依據美德之正義”,我們最后且聚焦在它們各自對于矯正之正義的見解。先從以下問題開始:一個善惡之人共存的社會為了實現正義應該做什么?關于這個問題,後面已經從儒家的角度提出了“關于美德之正義”的獨特概念。并且把善/惡與安康/疾病相模擬,認為某些人比其別人更有美德是不正義的,一個正義的社會應該從頭分派這些美德,從而使人人都能同等地(和最年夜化地)具有美德。風趣的是,從分歧的角度來看,儒家的關于美德之正義也可以視為矯正之正義:不具有美德的人或惡人在此被視為有品德缺點的人,他們類似于懷孕體缺點的人。把美德分派給他們,也就是使他們有德,這在本質上是對他們進行矯正。恰是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孔子與亞里士多德之間的第四點差異。這也是我要討論的最后一種差異。
亞里士多德認為不正義自己就是不服等,矯正之正義旨在恢復原有的(有比例的)同等。例如,假設張三和李四之間底本是有比例地同等的,現在假如張三從李四處偷了東西,張三就會獲得李四掉往的東西,從而導致不服等。矯正之正義請求,張三把所得的東西歸還李四以恢復最後的同等。同樣,假如“一方打了人,另一方挨了打,或許一方殺了人,另一方被殺了,做這個行為同蒙受這個行為兩者之間就不服等……法官就要通過法令的懲罰來達到均衡,要剝奪行為者的所得”【注87】,這般一來,同等又回來了。顯然,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就是現在所謂矯正正義的“報應”(retributive)理論【88】。這一理論與功利主義理論構成對比。報應理論是向后看的:恢復被不正義行為所擾亂的最後的同等;功利主義理論則是向前看的:避免將來發生不正義的行為。為了實現這一功利的目標,僅僅恢復原來的同等還不夠;有需要請求在不正義包養意思的買賣中已經有所獲得的當事人,也就是那個不品德的人、罪犯,放棄比他所得更多的東西,這樣才會禁止他及其他潛在的不品德的人和罪犯將來再做出同樣的行為。
眾所周知,這兩種理論各有利害。報應理論不克不及靠得住地避免將來統一個人或其別人繼續發生不正義行為,而這恰是功利主義理論的長處。但是,功利主義理論也難以證明,為什么我們可以迫使一個已做了一個不正義行為的人,不僅放棄他不應獲得的東西,並且還要被用作東西,放棄比所得更多的東西,從而禁止他本身將來再犯同樣的錯——更成問題的是,禁止其別人將來犯同樣的錯。恰是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儒家“關于美德之正義”的意義。作為一種矯正理論,這種儒家的觀點既非報應性的也非功利性的,而是還原性的、恢復性的或治療性的。【注89】這一觀點的最為獨特之處在于,雖然它也旨在矯正,但它要矯正的是不正義行為的本源,即不品德的主體,而大師熟習的兩種理論的矯正對象則是不正義行為的結果。這種儒家的矯正之正義優于報應理論和功利主義。矯正不品德的主體,也就是說,治愈其疾病,恢復其內在安康。假如做到這一點,一方面,他不僅不會再做出同樣的不品德行為,並且會成為其他能夠犯下同樣不品德行為的人的品德榜樣。這樣一來,我們不應用功利主義的手腕就可以達到功利主義的目標。另一方面,假如不品德的主體治好疾病,恢復品德安康,從而成為品德的主體,那么,他們天然會放棄他們不應得的東西,把它們歸還受益者。假如不克不及恢復受益者的損掉(例如,假如他們不品德的行為形成受益者掉往身體的某些部門甚至性命),他們也會盡力作一些適當的補償,同時也會為不品德的行為覺得自責、內疚和遺憾。是以,這樣一來,我們不應用報應論的手腕就可以達到報應論的目標。
結語
通過著重探討桑德爾的新亞里士多德主義正義理論的兩個重要特點,即“作為美德之正義”和“依據美德之正義”,本文供給清楚讀這一理論的一種儒家視角。為了進行比較,同時展現儒家思惟對當代正義話語的潛在貢獻,我盡量凸起儒家思惟和亞里士多德主義之間的差異,而不是它們的類似之處。不過,盡管在臺灣和噴鼻港仍有一些深受牟宗三師長教師(他能夠是最具影響力的當代儒家了)影響的學者尤其是儒家學者,認為儒家在康德的品德哲學框架內可以獲得更好的解讀,但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包含我本身在內,認為儒家與亞里士多德哲學最為契合。是以之故,我完整有能夠在本文中夸年夜了他們的不合。所以,假如我誤解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尤其是桑德爾所懂得的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和儒家的觀點其實完整分歧,那么我也會完整接收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注90】假如二者之間仍有一些差異,那么,我將站在儒家一邊,不是因為我是掛牌的儒者(我不是),而是因為本文所給出的來由,除非有朝一日我被相反的來由所說服。
注釋:
注1:Michael J.Sandel,“[Distinguished Lecture on]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1(2011):1303.
注2:Michael J.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34.
注3:Michael J.Sandel,Public Philosophy: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28.
注4: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186.
注5:盡管這是兩種分歧的目標論,可是,我們必須以一種適當的方法把二者聯系起來。與特定社會實踐相關的目標論必須服從于與人類目標相關的目標論,因為起首是后者決定一個特定的社會實踐能否應存在。否則,我們都可以分派竊賊團伙的領導權了(既然竊賊團伙的目標是偷盜,就可以獎勵、尊重和承認與此目標相關的品德)。克勞特(Richard Kraut)說得很好:“亞里士多德認為……,誠然,功績(merit)是解決特定問題的基礎,可是,畢竟應該把何種功績納進考慮則須參考整個配合體的配合善……一種分派物品(goods)的軌制之正義觸及兩個方面:起首,軌制必須有助于配合善;其次,分派所根據的功績標準必須從所要達到的配合善來看是適當的。假如一種軌制破壞了配合體的福祉,那么它就不合適正義的目標,即便它勝利地依照它所應用的功績標準來分派物品”(Kraut 2002:147)。
注6:桑德爾用的案例年夜都是關于獎勵善而非懲罰惡,不過他確實說過,“我們認為,那種攻其不備的行為應當遭到懲罰而非獎賞”(Michael J.Sandel,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9)。
注7:Michael J.Sandel,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0.
注8:Michael J.Sandel,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4.盡管桑德爾認為,那些高管獲得當局救助資金不是因為他們的貪婪,而是因為他們的掉敗。
注9:恰是在此意義上,帕克洛克(Michael Pakaluk)指出:“英語中的‘正義’一詞意味著:(1)正義的事態,即一種設定或狀況是正義的……(2)采取行動的意圖……或(3)品德或美德狀態,它引導或人帶著正義的意圖瞄準正義的事態。在希臘語中有分歧的字對應這三種分歧的含義。”(Pakaluk 2005:200)
注10: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3.
注11:Mark LeBar,“The Virtue of Justice Revisited”,In The Handbook of Virtue 包養女人Ethics,edited by Stan van Hooft.(Bristol,CT:Acumen,2014),270-271.
注12:桑德爾似乎贊同這一觀點,因為他曾說,“為了實現一個正義的社會,我們必須一路思慮完滿生涯的意義,并創造一種對難免產生的不合持友愛態度的公共文明”(Sandel,“[Distinguished Lecture on]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310)。
注13:當然,也可以說,既然羅爾斯把原初狀態設計為一種能夠衍生出正義原則的法式,那么,羅爾斯作為這個狀態的設計者的正義的美德就反應或表達在他的正義原則之中了。不過,羅爾斯顯然并沒有在此基礎上論證他的觀點。
注14: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398.
注15:Mark LeBar,“The Virtue of Justice Revisited”,274.
注16:Mark LeBar,“The Virtue of Justice Revisited”,272.
注17:Michael Slote,Moral Sentimen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25.
注18:《孟子·離婁上》。
注19:《孟子·公孫丑上》。
注20:Michael Slote,Moral Sentimen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26.
注21:Michael Slote,Moral Sentimen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26.
注22: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The Works of Aristotle 9(1963):1105a28-35.
注23:Aristot包養犯法嗎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The Works of Aristotle 9(1963):1105b5-8.
注24:《孟子·離婁下》。
注25:G.A.Cohen,If You’re an Egalitarian,How Come You’re So Rich?(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Chapter 8.
注26:本節中的論證,應用了法令和個人行為之間的模擬。正如正義的行為反應并體現了行為者的正義這種美德,正義的法令表達并反應了立法者的正義這種美德。不過,有一不類似之處:正義的行為源自個人,而正義的法令源自一群人,即立法者。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何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談論一群人的美德,即所謂的集體美德或軌制美德。這一問題無法在本文展開討論。關于該話題的一些有興趣義的討論,可參見Byerly 2016,Gregory 2015,Fricker 2010,Sandin 2007,Ziv 2012。
注27:例如,桑德爾提出以下問題:依據美德之正義能否只適用于榮譽而不適用于繁榮的結果?他接著指出,“爭論經濟設定的長短是曲經常把我們帶回到亞里士多德的問題,即人們在品德上應得的是什么,以及為何這般”(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3);然后,他當即失落頭討論上文提到的當局救市問題。
注28: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92.凱伊特也有類似的觀點:“對亞里士多德而言,分派正義起首關心政治權威的分派……其次才是財富分派”〔David Keyt,“Distributive Justice in Aristotle’s Ethics and Politics”,Topoi 4(1985):24〕;克勞特也說:“正義的重要問題,他(亞里士多德)認為是:誰應該擁有權力”;正因為此,亞里士多德“疏忽了一點,有時候分派不是基于功績,而是基于其他某個標準。假如食品和其他資源可供分派給需求的人,那么正義則請求把更多的錢給予那些有更年夜需求的人”〔Richard Kraut,Aristotle: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47,146〕。
注29: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53-166.
注30: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78.
注31: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79.
注32: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包養dcard78.
注33:普通認為,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討論了兩種特別的正義,即分派正義和矯正正義。與此分歧,斯旺森(Judith A.Swanson)認為,亞里士多德“承認三種(正義):分派、經濟和懲罰(正義)。當局關心分派正義,因為它分派職位和榮譽、權利和特權”〔Judith A.Swanson,“Michael J.Sandel’s 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A Response of Moral Reasoning in Kind,with Analysis of Aristotle’s Examples.”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1(2011):1377〕。雖然斯旺森分歧意桑德爾和凱伊特等人,主張經濟正義是亞里士多德的焦點關注,但她也主張,亞里士多德的經濟正義原則分歧于他的分派正義原則和懲罰正義原則。
注34:既然儒家的“關于美德之正義”觀念旨在替換桑德爾的“依據美德之正義”,它同樣與經濟好處的分派無關。
注35:《孟子·公孫丑上》。
注36:《王陽明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2),第2卷,第80頁。
注37:《孟子·告子上》。
注38: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05 b,第四章末尾。
注39: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29 a.
注40: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69 a..
注41:《王陽明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2),第2卷,第6包養違法8頁。
注42: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79 b5-515.
注43: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05 b21-23包養網單次.
注44: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80 a8.
注45:《王陽明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2),第17卷,第599頁。
注46:John Rawls,A Theory of包養合約 Justice,89.
注47:在儒家那里,修己和立人往往配合起感化,甚至密不成分。就此而言,斯洛特-加龍省的以下觀點為是:修己是不充足的;而他的以下觀點則非:儒家僅僅著眼于修己。他的后一觀點來自他對杜維明與艾文賀的解讀,他們都認為儒家以品德自修為焦點〔Michael Slote,“Moral Self-cultivation East and West:A Critique”,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2016):192-206〕。
注48:Huang Yong,“The Self-centeredness Objection to Virtue Ethics:Zhu Xi’s Neo-Confucian Response”,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84(2010):651-692.
注49:《論語·雍也》。
注50:《論語·為政》。
注51:《論語·顏淵》。
注52:《品德經》,第63章。
注53:李零:《喪家狗:包養網ppt我讀〈論語〉》(太原:山西國民出書社,2007),第62頁。
注54:李澤厚:《〈論語〉今讀》(噴鼻港:六合圖書公司,1999),第346頁。
注55:Huang Yong,Confucius: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London:Bloomsbury,2013),38-39.
注56:《論語·顏淵》。
注57:《論語·衛靈公》。
注58:其他文獻記載孔子如是說:“古之列諫者,逝世則已矣,未有若史魚逝世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不成謂直乎?”〔《孔子家語·困誓》(北京:北京燕山出書社,2009)〕
注59:《論語·陽貨》。
注60:《孟子·包養價格ptt滕文公下》。
注61:《左傳》(北京:中華書局,2長期包養007)襄公七年。
注62:《論語·子路》。
注63:Huang Yong,Confucius: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139-143.
注64:《論語·子路》。
注65:《孔子家語·三恕》。
注66:黃勇:“正曲為直:《論語》‘親親相隱章’新解”,《南國學術》3(2016):366—377。
注67:我要感謝德萊弗(Julia Driver),她的一個評論促使我想到了這個問題。
注68:只要置于這樣的脈絡之中,《論語》中的某些章節才幹獲得正確的懂得。好比,“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論語·衛靈公》);“正人求諸己,君子求諸人”(《論語·衛靈公》);“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論語·顏淵》);“樂道人之善”(《論語·季氏》),“惡稱人之惡者”(《論語·陽貨》)。在一切這些段落中,孔子不是說,我們本身有德就夠了,不需求做任何工作讓別人成為有德之人。相反,孔子是說,假如別人無德,我們就要責備本身,正如孔子所引的那句據說出自周武王的話:“蒼生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堯曰》)。
注69: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93.至多根據辛加諾的解釋,這一意義上的關于美德之正義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其實并不完整生疏,而在我看來,辛加諾的解釋是有事理的。因為對于亞里士多德,正義即同等,辛加諾認為亞里士多德對何為同等的答覆是美德,而“品德美德是正確軌制中正義的權衡標準。為了讓正義行于整個城邦,城邦必須為國民供給休閑及其他條件條件”(Marco Zingano,“Natural,Ethical,and Political Justice.”,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istotle’s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209-210)。他徵引亞里士多德為證:“無論是對于個體還是城邦,最好的生涯是一種美德生涯,同時配有參加美德活動所需的充足資源”(Politics VII 1,1323b40-24a2;Zingano 2013:209)。
注70: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8.桑德爾在其他處所提出更具包涵性的主張。例如,他說,有德之人“應該擁有最高的職位和榮譽,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會制訂明智的政策,使每個人都生涯得更好。也是因為政治配合體的存在,它至多部門地是為了尊敬和回報國民的美德”(195;黑體為筆者所加)。
注71:也許,它與其說是功利主義的,不如說是后果論甚至目標論的,因為儒家的目標在于尋求最佳后果或目標:使盡能夠多的人成為有德之人。顯然,儒家總體上屬于美德倫理,而后果論只在其美德倫理的總框架內發揮感化,而美德倫理的總框架是目標論的而非后果論的。
注72: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79 b5-10.
注73: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79 b31-1180 a4.
注74: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20.
注75:Michael J.Sandel,Justice:Wh包養女人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9.
注76: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79 b10.
注77:當然,這并不是儒家境德教導僅有的兩種方法。在別處,孔子提到了其他辦法。例如,他也說品德發展“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季伯》)。此處,除了禮儀規范之外,孔子還提到了詩和樂,二者皆屬于感情教導。除此之外,孔子并不是絕對反對懲罰性法令,因為他意識到有時懲罰性法令是需要的。但是,他認為,在幻想情況下,這種法令僅僅是在場的,而不是被運用;當確實需求運用它們時,它們只是臨時起到補充感化。無論是在不得不運用這種法令手腕之前或之后,都必須要用其他品德教導手腕。
注78: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80 b13-15.
注79:《論語·子路》。
注80:《論語·顏淵》。
注81:《論語·子路》。
注82:《論語·為政》。
注83:當然,這并不料味著儒家認為品德美德是政治領袖所必須擁有的獨一東西。除了使國民變得有德之外,當局的目標還促進社會正義,特別是正義地分派經濟好處,這就請求政治領袖具備相關的專門知識。當然,在儒家看來,品德美德對政治領袖來說不僅是需要的和最主要的,並且它天然會引導政治領袖探尋能夠正義而有用地管理社會的專門知識。
注84: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94.
注85:Michael J.Sandel,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326.
注86:感謝德萊弗(Julia Driver),她的評論促使我想到了這個問題。
注87: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32 a7-9.
注88:是以,他說:“人們總是尋求以惡報惡,若不克不及,他們便覺得本身處于奴隸位置。人們也尋求以善報善,若否則,買賣就不會發生,而恰是買賣才把人們聯系到一路。”(1132b34-1133a2)
注89:應當指出,不言自明的是,我們的意思分歧于與桑德爾的刑事正義治療理論。在桑德爾那里,治療訴訟“把懲罰看作是受益者的一種撫慰,一種暢快的表達,一種終結。假如懲罰是考慮到受益者的好處,那么受益者在決科罪犯該受何種懲罰時就有發言權”(Michael J.Sandel,Public Philosophy: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106)。簡言之,在桑德爾那里,接收治療的人是受益者;而在孔子那里,接收治療的人是加害者。
注90:這是完整能夠的,桑德爾有時也會提出類似的主張。例如,他在討論一位受歡迎的重生拉拉隊隊長斯馬特(Callie Smartt)的事例時說:“在選擇本身的拉拉隊隊長時,高中學校……表達了它盼望學生們往欽佩和效仿的質量。”(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86;黑體為引者所加。)他還把亞里士多德對于正義包養網單次的進路描寫為“分派物品以獎勵和促進美德”(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08;黑體為引者所加)。是以,當桑德爾說分派政治職位以尊敬、獎勵和認可相關的美德,我們應該將之更好地輿解為,他是在說,經由分派促進相關美德,需求通過尊敬、認可和獎勵那些擁有相關美德的人,這樣別人就會效仿他們。假如是這樣,我們可以說,桑德爾的觀點和儒家的觀點完整雷同。但是,即使這般(似乎這般),我們也不克不及忽視它們之間的一些細微差別。一方面,依照桑德爾的理論,其別人會效仿有德之人,因為有德之人獲得了政治職位這樣的獎品。假如他們對這樣的政治職位不感興趣,他們就會缺少效仿有德之人的動機。而依照儒家理論,有德之人應該掌管政治職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典范行為可以更好、更廣泛地為通俗蒼生所效仿。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答覆一個問題:這些政治領袖要具備什么樣的相關美德?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桑德爾的亞里士多德模子中,因為這些政治職位所要獎勵、承認和尊敬的美德,是那些與立法者相關的美德,它們也必須是當局促進和鼓勵人們往效仿的美德。可是,考慮就任何社會在任何時候都只需求少數人來制訂法令,每一個國民真的都需求有這樣的美德嗎?相形之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儒家形式中,政治領袖應該具有的美德和他們想讓通俗人擁有的美德乃是品德美德。無論是政治領袖還是通俗人,為了成為一個安康的或沒出缺陷的人,都必須包養管道具備這樣的品德美德。
作者注:2016年3月,本文初稿在華東師范年夜學舉辦的“桑德爾與中國哲學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andel and Chinese Philosophy)上宣讀。會上,桑德爾傳授提出了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和評論,這使我的論文修正受害很多。2016年8月,在湖北年夜學舉辦的“國際美德倫理高端論壇”上,德萊弗(Julia Driver)傳授在評議拙文時提出了一些有興趣義的問題,我的有關思慮現已融進到定稿之中。斯洛特傳授列席了后一次會議,本文(尤其是第二節討論其觀點的部門)也受害于與他的交談。同時,本文亦感謝李晨陽傳授的評論。該文的英文稿2018年將發表于Encountering China:Michael Sandel and Chinese Philosoph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Edited by Michael J.Sandel,Paul J.D’Ambrosio;Foreword by Evan Osnos.經原編者、作者和哈佛年夜學出書社授權,在《南國學術》先行註銷中文稿,由華東政法年夜學校報編輯崔雅琴翻譯。
相關鏈接
【桑德爾】亞里士多德、孔子與品德教導——對黃勇傳授的回應
責任編輯:姚遠















-88.jpg!article_800_auto)

-59.jpg!article_800_auto)
-56.jpg!article_800_auto)
-100.jpg!article_800_auto)
-54.jpg!article_800_auto)
-42.jpg!article_800_auto)
-72.jpg!article_800_auto)